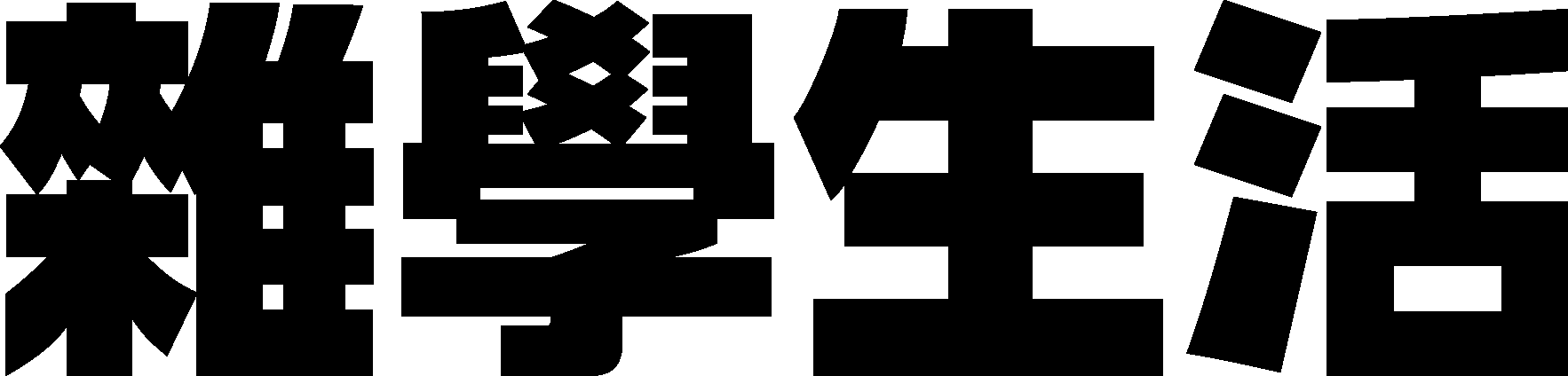談到哈維爾.馬利亞斯的《如此盲目的愛》,許多人都會引用書中一段話。在書中,這段話第一次被說出,是迪亞斯.巴雷拉跟瑪麗亞講述巴爾札克的短篇小說:夏貝爾上校在戰役中被誤判死亡,又企圖回到她妻子身邊的故事。第二次是瑪麗亞想起《三劍客》裡伯爵夫人被劊子手處死的情節,又想起迪亞斯.巴雷拉說過的這段話。第三次已經接近書的結尾,迪亞斯.巴雷拉跟瑪麗亞坦承,他覬覦好友的妻子路易莎,所以「啟動」了米蓋爾.德思文慘死街頭的謀殺案,但這件事不光是迷戀沖昏了頭,背後,還有個屬於迪亞斯.巴雷拉跟米蓋爾.德思文這對好兄弟之間,看似情義相挺的正當理由,瑪麗亞聽著幕後兇手的單方面說法,推敲著謊言跟實話時,「也許他現在正在告訴我真相,為的是讓它像謊言。似乎很像謊言,似乎就是謊言。」作者又一次引用了這段話:
發生了什麼是次要的,小說裡發生的一切無關緊要,小說一看完就忘了,重要的是小說通過虛構事件告訴我們、灌輸給我們的可能性和想法比真實事件更清晰地留在我們的腦海,我們對之更加關注。
當然,說小說裡發生的一切無關緊要是太過武斷,像是開了讀者一個大玩笑,但重點是我們必須留意哈維爾.馬利亞斯所謂的「灌輸給我們的可能性和想法」,這種關於文本的解讀通常是作者起了頭,接下來就得靠讀者自己去各自生活中探索、挖掘,或是對照人生際遇中的真實情節。馬利亞斯到底想說什麼?書中最顯而易見的主題當然就是死亡,就像在他另一本《如此蒼白的心》,故事開頭就直接拋出了一具屍體,這回他關注的是恩愛的夫妻如何面對另一半的突然死亡,如何能掙脫亡魂繼續往前走(亡者的力量是生者給予的,亡者就是徹底死了,一切都是生者內心的糾結),讓人難過的不只是死亡這件事,而是有一天妳突然感受不到原本以為走不出的傷痛,發現已經將他徹底遺忘了,繼而產生背叛死者的愧疚感,「但願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漸衰退的記憶。我為自己分分秒秒地疏漏萬物向時間致歉。我為將新歡視為初戀向舊愛致歉。」連辛波絲卡都用了包容與致歉的詞句,或者,容我引用另更殘忍的說法:亡者通常會死兩次,一次是肉體的死亡另一次就是生者將他遺忘。但如我一開始爆雷的,這不是單純的死亡;是一樁殺案!較之一般的死亡更不容易被遺忘,即使這不是偵探推理小說,但我們總是想揪出凶手,了解背後喪心病狂的動機。作者藉由瑪麗亞讓我們聽到兇手跟幫兇的對話,目的不是要我們急著將死者的好哥們迪亞斯.巴雷拉非黑即白地定罪,或許比較接近作者企圖的讀法,是把它當作「假設題」:發生什麼是次要的,迷戀作為動機,它可以把人推到甚麼樣痴狂的境界,甚至就是書中犯下的罪行,旁人該如何評斷?

關於迷戀,有太多小說或電影可以找到不同的故事架構或切角,音樂史上的《幻想交響曲》無疑是白遼士留給後人的一篇勵志故事,小說裡,馬奎斯的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、帕慕克的《純真博物館》、納博科夫的《蘿莉塔》、符傲思的《蝴蝶春夢》,不同作者的作品都為這個題目展開申論及推敲(灌輸給我們的可能性和想法)。馬奎斯跟帕慕克筆下的主角類似我們今天嘲諷說的「工具人」,只是默默守在迷戀對象的身邊,對抗著時間對熱情的消磨,期待她終有一天會回眸一笑。納博科夫跟符傲思狠了些,《蘿莉塔》裡的韓伯特先是要將他的手伸向十二歲的女孩,還要除去作為他妻子或說是岳母的這個角色,《蝴蝶春夢》的佛瑞德更直接囚禁迷戀對象,將她視為蝴蝶標本。在馬利亞斯筆下,作為這樁謀殺案「始作俑者」的迪亞斯.巴雷拉同樣有著堅強的意志,他是這麼替自己辯解,而這自白對路易莎來說,未嘗不是人生中最深情的告白,但故事中的她是絕不該聽到的。
我很清楚我只愛一個女人,就是路易莎,我很清楚不能靠運氣,不能指望事情自己發生,不能指望障礙和阻力會神奇地消失。你得自己去努力。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是懶人和悲觀者,他們一無所獲,因為他們不勤奮,然後便大肆抱怨,覺得很挫敗,對外界懷恨在心:大多數人都是這樣,都是遊手好閒的白癡,提前被自己的生活定位和擊潰。這麼多年我一直單身;是的,我在等待,期間有一些愉快的風流韻事讓我暫時忘掉痛苦。最初我在等待一位讓我鐘情,我對之情有獨鍾的人出現。後來……對我來說,這是我承認那個詞語的唯一方式,所有的人都在隨隨便便地使用這個詞,但是它不應該如此簡單,因為許多語言中都沒有它……el enamoramiento——墜入情網,或是迷戀的狀態。我指的是這個名詞,這個概念;它的形容詞,即它所指的狀態大家確實更為熟悉,至少法語中有,英語中沒有,但是有些詞在努力表達它,意思很接近……很多人令我們很有好感,讓我們開心,令我們著迷,激發我們的感情,甚至打動我們,或者讓我們喜歡,吸引著我們,甚至讓我們一時瘋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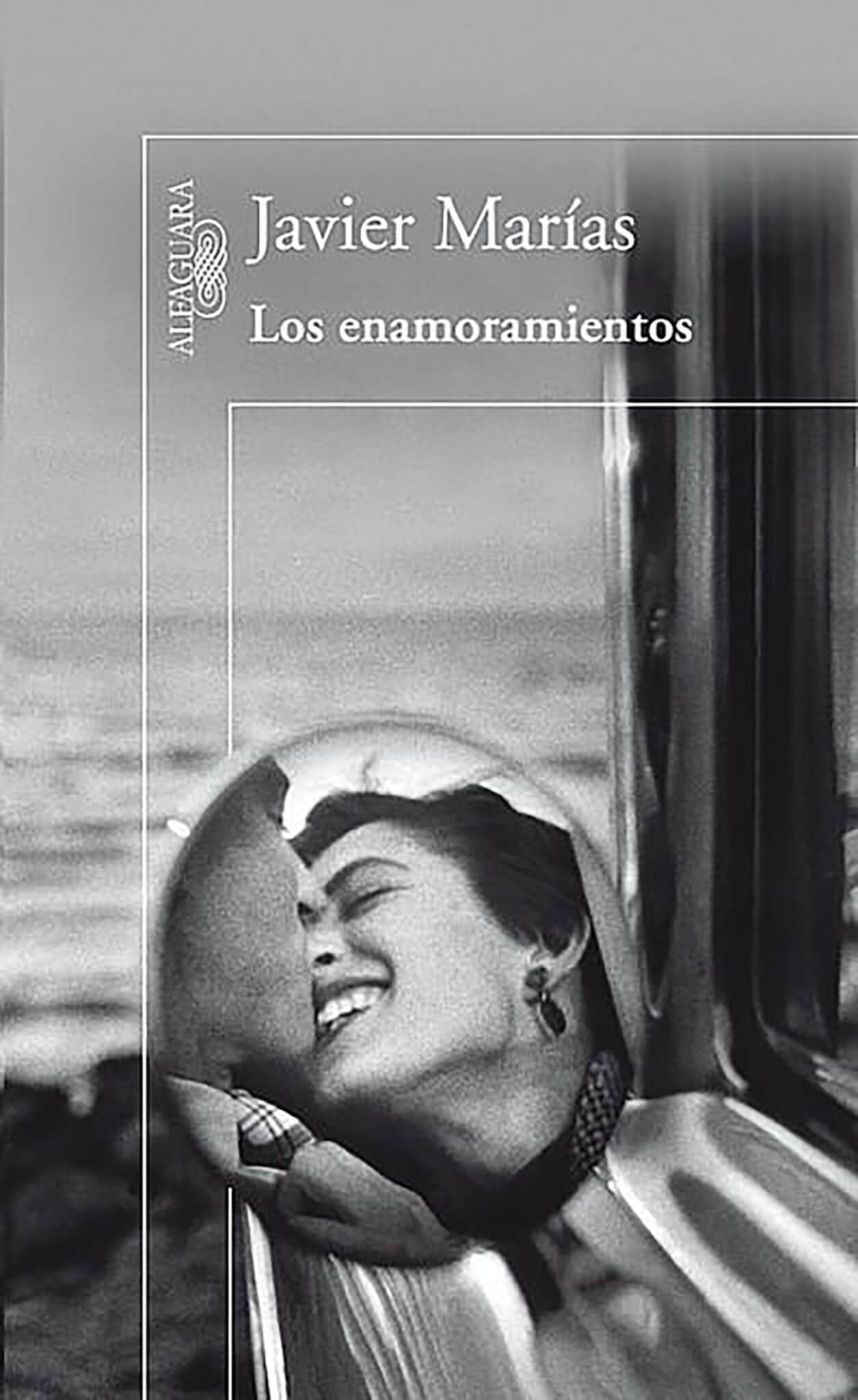
迪亞斯.巴雷拉對瑪麗亞坦承他的罪行後,迷戀不僅是迪亞斯.巴雷拉犯罪的動機;也是瑪麗亞糾結著要不要揭穿迪亞斯.巴雷拉惡行的牽絆。對大多數的人來說,這件謀殺案就是一名流浪漢認錯對象的悲劇,迪亞斯.巴雷拉會擔起責任好好照顧米蓋爾.德思文的遺孀路易莎,周遭親朋好友也會收好悲傷繼續地前進,可以畫下一個不完美但勉強接受的句點。瑪麗亞如果跟警方或路易莎抖出這個祕密,可以說是伸張正義,但又為何不是因為迷戀迪亞斯.巴雷拉,忌妒他即將跟路易莎共度餘生而「啟動」了另一件自私的行動?這麼一樁兇殺案有了兇手有了動機,卻也產生了更多的不明確。像是納博科夫的《幽冥的火》,一首九百九十九行的長詩,又被加上了喧賓奪主的十多萬字註解,到底甚麼是真是假?或是這些真與假的意義為何?身為讀者的我們當然也有權利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小說裡發生的「一名男子因迷戀好友之妻,而藉他人之手殺了好友」,這時如果還死守著公平正義或不容許汙點的道德觀,或是「你們當中誰是沒罪的,誰就可以用石頭扔她」的恐嚇,還真是浪費了這本小說,而我,想借用《蘿莉塔》裡韓伯特為自己的辯白,來表達我對《如此盲目的愛》的喜愛,「我現在不是,從來也不是,將來也不可能是惡棍,我偷行過的那個溫和朦朧的境地是詩人的遺產——不是地獄。」當然,它可以是一個角色的獨白,或者你可以將它視為人類某種意志不受拘束的想法,「重要的是小說通過虛構事件告訴我們、灌輸給我們的可能性和想法比真實事件更清晰地留在我們的腦海」換句話說,所有的故事的情節都是沙土、木材、磚瓦、鐵件等材料,目的是為了建構出一座莊嚴的聖殿,在裡面供奉這些由人創造出卻又捉摸不定的神祇,隨著時間的流逝,有一天聖殿會坍塌,在整個世界熬過了《百年孤寂》後,應該能更清晰地看清楚這盲目的愛情。
背影是真的 人是假的 沒什麼執著 一百年前你不是你 我不是我
悲哀是真的 淚是假的 本來沒因果 一百年後沒有你 也沒有我
《如此盲目的愛》(Los enamoramientos), 是西班牙作家哈維爾.馬利亞斯(Javier Marías)的作品。馬利亞斯是公認開拓敘事「形式」的大師,他用小說開創一種「思考性文體」,華麗而饒富韻律的長句,不斷插入漫無邊際的哲學思考,中斷我們對於情節或人物連續性的認知。